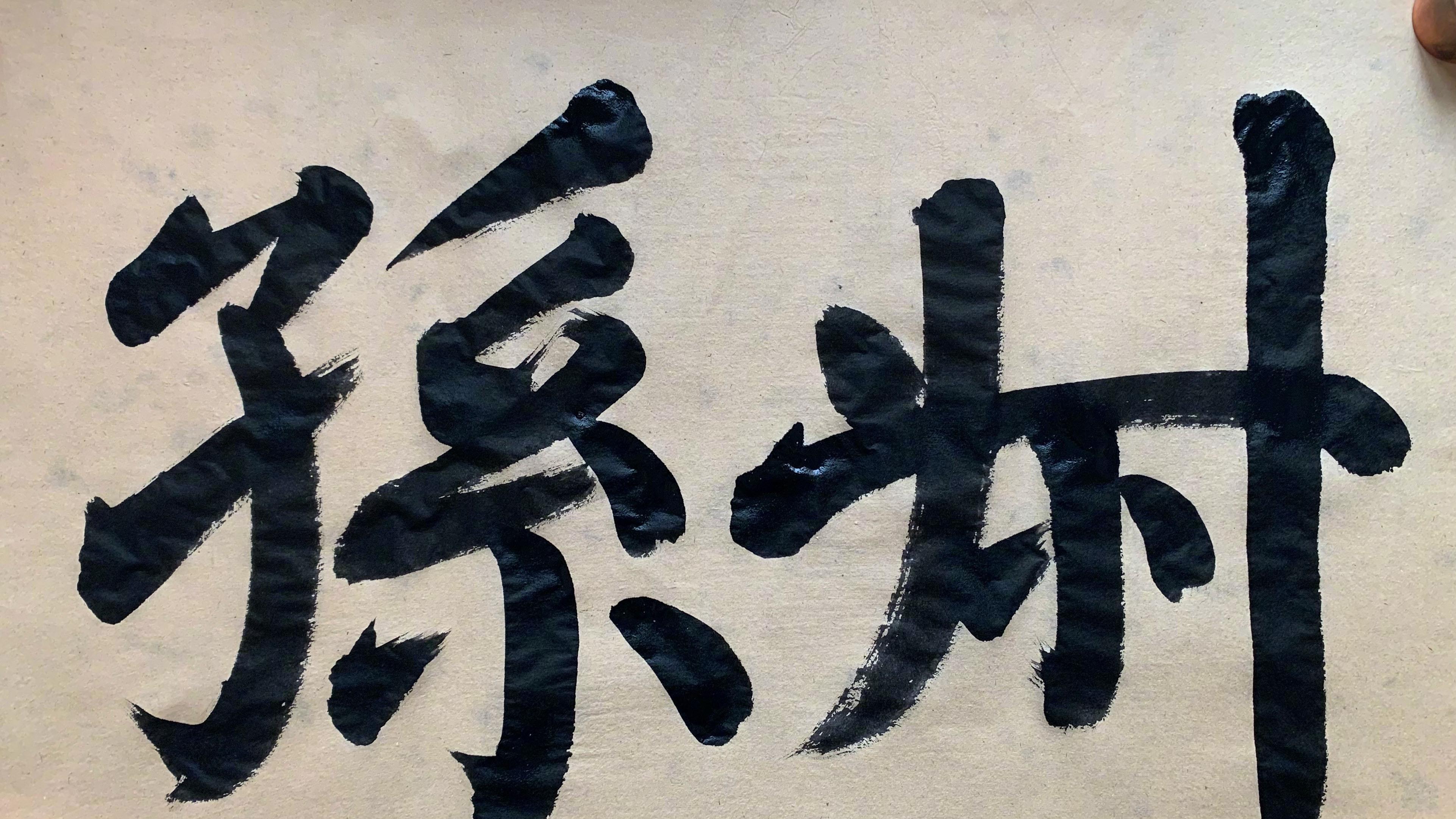電影《流浪地球》系列,雖然掛名是改編自劉慈欣的小說,但實際上在悄然無聲之間,偷偷摸摸地改換了小說原著的設定。
為什么要作出這樣偷偷摸摸的改換?
這是因為劉慈欣小說里,深刻地飽含著強烈的悲觀主義情結(jié)。
甚至《三體》的最大改編難度也在這里。

因為《三體》里同樣寄寓著劉慈欣的根深蒂固的悲觀情結(jié)。在《三體》里,劉慈欣洋洋灑灑傾訴的主題,是劉慈欣對寄生在韜光養(yǎng)晦大基調(diào)下如何逃得生天的被動應對策略的諸種選項的排列與組合。如何逃生,構成了整個小說的隱性主題,在這樣的對生存至上的宣泄與張揚的基調(diào)下,必然決定了小說的外在的形象與文本里,都充斥著濃重的悲觀情調(diào)。
要把這種逃生諸種選項,改編成一個能夠可見可觀、符合大眾價值觀的電視劇,難度可想而知。
這種悲觀的基調(diào)與定調(diào),也濃重地涵容在《流浪地球》小說原著里。
改成電影,必定要有英雄主義、集體主義、樂觀主義的情懷,不然,進入電影院的觀眾,走出來的時候,都患上了抑郁癥,這樣的電影顯然是不會討人喜歡,最終將會受到票房的致命絕殺。
走商業(yè)化道路的電影,誰都不敢冒這個險。
所以,商業(yè)電影的主題定調(diào),必定符合社會的主題基調(diào)與民眾的心理接受程度。

正是在這樣的拍片意圖之下,《流浪地球2》當然包括之前的《流浪地球1》,都對劉慈欣原著里的悲情基調(diào)作了堅決的棄決。
我們暫且將這種棄絕歸納為三個方面:
一是派別爭鋒的主題作了置換。
《流浪地球》小說原著里,最奪人眼球的,固然是用12000臺地球發(fā)動機,驅(qū)動地球,離開太陽系,開始了孤獨飛往外星系逃生的這一“敢叫山河換新天”的設定,但是,依附于這一自然的奇思妙想之上的,是人類文明自誕生之日起就如影形隨的觀念的爭鋒。
在小說里,地球流浪的爭鋒焦點是:飛船派與地球派。
飛船派的主要企求,是用飛船逃生,而地球派,是驅(qū)動地球去逃生。
最終,地球派占了上飛,從而使地球的流浪正式踏上征程。
但是,這兩種交鋒,在小說里原著里,終于不可調(diào)和地展開了你死我活的搏斗與殘殺。在地球流浪的途中,飛船派發(fā)動了叛亂,攻擊占聯(lián)合政府主流思想的地球派,最終飛船派獲得了勝利,將地球派的殘存人馬一網(wǎng)打盡,全部處于死刑。
劉慈欣借助于這個情節(jié),揭示了人類世界中的固已有之的傾軋與爭斗,即使在命在旦夕的危難之際,也要像毒液一樣,爆發(fā)出來。
這是對人類文明的一種絕望的認知。
到了電影《流浪地球2》中,顯然不能照搬劉慈欣小說原著里的殘酷的設定。電影甚至改編了人類爭鋒的模板,將劉慈欣原來設定的飛船派與地球派的交鋒,轉(zhuǎn)化為“數(shù)字生命派”與“地球流浪派”之間的理念碰撞。
顯然可以看出,《流浪地球2》扭轉(zhuǎn)了《流浪地球1》中的不足與缺陷。

《流浪地球1》更像是一次試水的作品,專注于的是一次災難的展示與顯擺,視線主要集中在劉啟的身上,無暇顧及到更為全景式的“流浪地球”的來龍去脈的考量與揭橥。
這也導致了《流浪地球1》里的視線單一,情節(jié)單線條發(fā)展,人物情感也相應地單維度遞進。
《流浪地球2》試圖從更廣闊的社會層面,揭開地球流浪背后的不同理念的交鋒。
而小說原著中的飛船派與地球派的沖突,都是一種集中于不同逃亡手段之間的沖突,是一種逃亡載體之間的爭論。顯然,這種逃亡的方式,其實有一點是共同的,差距并不大,那都是一種人類的肉體的移行與逃亡。
而現(xiàn)在《流浪地球2》里的逃亡沖突的改動,卻從原著中純粹是肉體之間的逃亡,轉(zhuǎn)化為“靈與肉”的逃亡之別。
“數(shù)字生命派”里,人類的肉體盡可以拋棄,可以把一個人的生命,轉(zhuǎn)化為一種意識的存在,然后讓這個代表著人的全部的意識進行逃亡,就可以完成生命的不滅了。

這與帶著地球逃亡的肉體一派,顯然拉開了巨大的差距,也構成了《流浪地球2》里的沖突的波詭云譎。
這種沖突,也更加勢不兩立,你死我活。作為可視形象的電影來說,也為“數(shù)學化人生”的設計,帶來了更容易找到前科的科幻傳統(tǒng)積淀,讓《流浪地球2》的理念級別,接榫上了世界電影里最流行、最時髦的源起于人類的“靈與肉”這一哲學根本沖突的虛擬生命的龐大種屬。
這也為《流浪地球2》里平添了劉德華主導的“數(shù)字生命”的線索,帶來了可能。
這樣,《流浪地球2》里便不是《流浪地球1》里的大逃亡式的單線發(fā)展的情節(jié)結(jié)構,而是在不同理念的交鋒輪番遞進的互動中,推進著影片的內(nèi)在的立體空間的前行與演繹,相對而言,《流浪地球2》里的內(nèi)在結(jié)構更為豐富,更為立體,也更為膠著。
二是地球災難的形式作了置換。
《流浪地球2》與之前的《流浪地球1》里都出現(xiàn)了一個“洛希極限”的名詞,而在原著里,并沒有提到這個“洛希極限”。
“洛希極限”自然有更為科學的解釋,但通俗地講,“洛希極限”,意味著兩個星球在靠近的時候誰俘獲誰的問題。
也就是說,“洛希極限”一過,那么,弱勢的星球,就會被強勢星球俘獲而去。
“洛希極限”對于科幻作品來說,意味著星體之間的平衡被打破,生死存亡的危機啟動。

一個巨大的死亡陰影,藏在“洛希極限”后邊,席卷而來,這構成了《流浪地球2》及《流浪地球1》里的最大的危機突降。
相對而言,《流浪地球》的小說原著,更多的顯擺的是作者劉慈欣對地球流浪的連根拔的想象力得瑟。從某種程度上講,劉慈欣是通過“地球流浪”進行了一次惡搞。之前,在世界上科幻作品炮制毀滅地球的災難的時候,能夠采取的拯救措施,都是一種小修小補式的個人英雄主義拋頭露面。但劉慈欣更為釜底抽薪,把所有的好萊塢科幻片里的大呼小叫的拯救地球方式,都襯托出小兒科的可笑,直接將地球給撬動了,如此驚天動地的想象,不能不說與中國人骨子里有一種“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的文化想象有著密切的關系。劉慈欣只不過把我們過去的藐視與輕視“小小寰球”的意識形態(tài),轉(zhuǎn)化為煞有介事的科幻想象罷了。
作為殘存著理智一面的劉慈欣在寫作《流浪地球》的時候,也曾經(jīng)猶豫不決,差一點半途而廢這一“拆遷地球”的酷烈想象,但是,他終究拗不過這一“酷烈”的惡搞所帶來的快意,還是把這一匪夷所思的想象,化成了文字,公之于眾。
但是,在小說原著里,流浪地球的想象,已經(jīng)足夠富有戲劇性,但拍成電影之后,便沒有一個激烈的戲劇沖突點,這時候,“洛希極限”這一救命稻草便被祭出來了,以作為拯救電影的戲劇結(jié)構了。
《流浪地球2》及《流浪地球1》里的危機沖突,幾乎是一個模子脫出來的,《流浪地球2》里,月球在靠近地球的時候,突破了“洛希極限”,地球命懸一線,必須在月球穿過極限的時候,摧毀月球。《流浪地球2》里,用生命摧毀月球,構成了電影的最為核心的情節(jié)沖突,也在這個危機之中,凸顯了人類的精神質(zhì)量。

而在小說原著中,只是輕描淡寫地提到月球被輕而易舉地移出了地球的軌道,根本沒有電影里的那一場月球與地球的相撞風險。
而《流浪地球2》里的這場月球撞向地球的情節(jié),是《流浪地球1》里最重要的沖突的翻版。《流浪地球1》里,是地球流浪到木星的時候,也因為兩個星球突破了“洛希極限”,地球撞向了木星,地球流浪計劃面臨著功虧一簣的危險。幸好吳京扮演的劉培強,用自己的生命,阻止了這種“星星相吸”,完成了對地球的拯救。
而在《流浪地球2》里則是劉培強的戰(zhàn)友,用自己的生命完成了對地球的拯救。
因此, “洛希極限”在《流浪地球2》及《流浪地球1》里兩次用于同一目的,都是為了平添一個原著里沒有的即時性的危機,為英雄的出現(xiàn)創(chuàng)造條件,制造出電影里的催人淚下的感人篇章。
而這種感人段落并不是劉慈欣小說里隱伏著的敘述真諦,因為劉慈欣的悲觀主義情結(jié),導致他在小說里并沒有著意于以拯救天下為已任的英雄主義的張揚與倡導,這就涉及到本文的第三點,電影對劉慈欣小說中的道德觀念與價值體系作出了重新設定。

三是道德觀念的定調(diào)作了置換。
《流浪地球2》里陳述的犧牲精神、合作精神、團結(jié)精神,是電影張揚的一個主題。
電影里中國領航員一馬當先地喊出“五十歲以上出列”的英雄氣概,振聾發(fā)聵,響遏行云,身著中山裝的李雪健扮演的中國形象的代表,也有一句口頭禪“危險當前,唯有責任”,其內(nèi)在的言語本質(zhì),我們也能耳熟能詳。
但有意思的是,這一切,在劉慈欣的小說里都不存在。
劉慈欣在小說原著里渲染的是一種末世懷結(jié),作者強調(diào),在人類缺乏一個安全的世界里,人類的精神文化,處于一種崩潰的狀態(tài),道德觀念與價值體系,已經(jīng)早就先地球而開始流亡了。

劉慈欣的小說原著里提到一個情節(jié),“我”的父親在地球流亡的朝不保夕的陰影之下,突然有一天,離開了母親,而與自己的女老師過了一段同居生活,小說里寫道:“每個人都在不顧一切地過自己想過的生活,這也沒有什么不好。”
接著小說對地球流亡時代的人類道德,發(fā)起了一段議論:“在這個時代,人們在看四個世紀以前的電影和小說時都莫名其妙,我們不明白,前太陽時代的人怎么會在不關生死的事情上傾注那么多的感情。當看到男女主人公為愛情而痛苦或哭泣時,我們的驚奇是難以言表的。在這個時代,死亡的威脅或逃生的欲望壓倒了一切,除了當前太陽的狀態(tài)和地球的位置,沒有什么能真正引起我們的注意并打動我們了。這種注意力高度集中的關注,漸漸從本質(zhì)上改變了人類的心理狀態(tài)和精神生活,對于愛情這類東西,我們只是用余光瞥一下而已,就像賭徒在盯著輪盤的間隙抓住幾秒鐘喝口水一樣。”

在小說原著里,“愛情”等等人類的道德規(guī)范與準則,都棄若弊履,不復為人類珍惜。這種基調(diào),在《流浪地球2》及之前的第一部組成的兩部電影中都被掃蕩而空,而讓英雄主義、犧牲精神站到了前臺,與之相配合的是,能夠展現(xiàn)出英雄主義氣度的“洛希極限”便被電影拿來作為一個襯托工具,一而再、再而三地構成電影的危機態(tài)勢,讓“滄海橫流,更顯英雄本色”的英雄生成原理得以在電影里大行其道。

《流浪地球》 系列更像是移用了小說原著的陰澀的創(chuàng)意基調(diào),進行了商業(yè)化需要的進取精神的重新修飾,構成了電影工業(yè)化能夠擄獲受眾的一種最大公約數(shù)的模式體系。電影里更多地摻雜著集體的能夠被時代認可的共性思維,而小說原著,更多地云集著作者的發(fā)自個體的悲觀想象,這就是電影對原著移用了硬核體系而對小說里的軟件部分進行了重新的迎合時代的改寫的原因。